| 总站·浙江在线 浙江网闻联播 《浙江日报》 《丽水日报》 《处州晚报》 ;新闻热线:0578-8061733 8062468 投稿邮箱:zgsynews@163.com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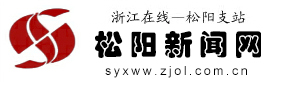 |
|
|
松阳旧市街的张家墙弄 凝固在建筑上的历史 古市镇是松阳县在东汉建安四年置县时的县治所在地,邑人以“旧市”称之,在古市西北处有一旧门楼称“城门楼”,城门楼与下街之间的三百余米长的街巷,称之城头街,在城头街两侧有天灯弄、天灯下弄、五福弄、项门弄、三角石玄弄、耶酥堂弄、耶酥堂下弄和城门弄。其中,与项门弄相接,与城头街平行的一条弄叫张家弄,也称之张家墙弄。清代文人叶孝先在《古市志略》中提到,“若塘岸吴族、城头洪族、张族、林族、观口廖族,均清初及中叶新建者。” 城头张族即为张家墙弄的张族,经过几代的发展,到了清末民国初年,张氏已经是城头的望族了。当时,古市镇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叶家顶、张家屋、洪家谷、詹家芋配粥。这四个姓,至少是那个时代古市镇几个大家族的代表,意思是叶姓的当官为多,张姓的房子多,洪姓的田地多,詹姓的比较穷,祭祖的时候只摆放了芋和粥。 张家弄在古市镇算得上宽敞,巷弄宽敞许是为门口停轿系马而准备的,就像现代的停车位一样重要。之前,在项门弄拐进张家墙弄的转角处,放着五块百余斤重的大石头,供大家休息纳凉,现在这五块石头已经不见。只见一排有着高大门墙的房屋映入眼帘,四幢毗邻的张家大屋均各自有出入的正门,但屋与屋之间有小门相通,现在首间的大屋因建设松州路已经拆掉了,第二间也已经改造过了,第三幢的墙体还是当初的,门额上题着墨色的“百忍旧家”,这表示张姓的堂号是百忍堂。第四幢也是石库门,有两个天井,第一进为三间两厢对合式,第二进为三间两厢,皆为二层。这户人家目前只有一个叫张来福的老人住在此处,他一个人住在外堂,杂物都堆放在天井、过道等处,连饭都放在檐廊下烧,檐下的牛腿等木作都被几十年的烟火给熏得乌黑。 第二进现在已经没人住,土改后,叶氏、詹氏、王氏、高氏等人分得那里的房产,不料几十年来,各家都有晦气的事情发生。后来,有人在房梁上发现一个机关,据说正是这个机关,导致了住在此宅的人交上了霉运。张来福说,以前内堂的太公是个很恶毒的人,曾经将一个丫头活埋在天井花坛处,所以每天五点钟,都有丫环的冤魂出来梳头……但外公家在张家墙弄的戴更新老人告诉我,梁上的机关也只是里人传说,没有人见过。我将那个“机关”拍下来放大,似两个桃子形状的空洞,据说是梁上钉着挂东西的钩,按道理是不用中空的,为何做成中空,张来福、戴更新等老人都不太明白。 我有个姓蓝的同事就在张家墙弄长大,住在张家大屋后面的辅房中,张家的地主打倒后,他的父亲作为贫下中农分得几间辅屋,还有几家贫下中农则住在第二进的主房、厢房里,七十年代,这些年纪相仿的孩子在“百忍旧家”的宅子里捉过迷藏,元宵节时过龙灯拿过红包在宅子内游走,所有的松阳节气的习俗都在那幢房子里演绎过。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孩童的声音一个个地消失在石库门外,有的长大成人到外面工作,有的如那个传说一样,遇到各种意外。第二进因为缺乏人气,建筑渐渐衰老,有的墙体倒塌,有的屋檐残缺,天井处居然杂草丛生。 张家对面的是汪姓的地主家,房子也是一幢幢连成一排,屋内有小门贯通。一个住在汪家大宅的53年的老妇告诉我,以前来抓壮丁的时候,张家墙弄的壮丁都抓不去,就是靠了这些相通的门,这头进去,另外一头就出去了。 在汪家大宅的边上,一幢门牌为18号的宅子,门额上题着“瓯青公所”,此公所为民国之前的青田商人和船夫所建,在航运鼎盛时期,松阴溪及松阳的烟叶产业等,曾使松阳一度繁华,县域内产生了由各地的客商组成的商会,以及各商会办公所需要的机构,“汤兰公所”、“临天栈”、“汀州会馆”、“江西会馆”以及县城及古市的“瓯青公所”均为其缩影。古市的“瓯青公所”为何独独相中了张家墙弄,这个原因已经无人知晓,但张家墙弄的汪、张两个家族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张家墙弄的百忍与不忍 与张家墙弄有关的两个女子不得不提。一个是出生在“百忍旧家”的民国女子张玉瑛。 张玉瑛的爷爷和父亲主要经营烟叶生意,家族靠着经营烟叶发家致富,她爷爷膝下共有七个儿子、二个女儿,她父亲排行第二。1933年,时年芳15的张玉瑛高小毕业后,随着姑父叶忠莲来到上海纺织厂工作。叶忠莲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氏兄弟经营的九家纺织厂负责安装维护进口的纺织机,并为荣家所倚重。聪颖的张氏一边上班,业余时间多泡在工厂的图书馆里,并且当时工厂的文化生活也很丰富,她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里,在繁华的大上海看了很多由胡蝶、周旋、阮玲玉、白杨等人主演的默片,张玉瑛虽然出身于小县城,却受到大城市文化的熏陶,对于自小酷爱阅读的人来说,一个工厂的图书馆又很好地满足了她的阅读需求。 在张玉瑛抵达上海的那一年,古市一个姓戴名贤字思齐的年轻人投笔从戎到南京投奔钟松将军,初任上等兵,后考入黄埔军官学校通讯科,毕业后任无线电报务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荣家纺织厂西迁至重庆,张玉瑛选择了回松阳。与此同时,在“八一三”上海沪淞大会战前,戴贤随陆军独立第廿旅钟松将军所率领的三个团坚守在南市一带,经受住了日军的狂轰滥炸,1938年3月,戴贤参加了徐州会战,9月前往大别山麓的河南省固始县,执行阻击日寇、保卫大武汉的任务,年末,在陕西省兴平县进行休整。在兴平县休整的时候,戴贤将自己的心思告诉了前来投奔钟松将军的老乡,张玉瑛的六叔,因张玉瑛的大哥与戴贤本是同学,两人自小熟悉,于是钟松将军作了他们的证婚人,张家六叔为主婚人,俩人在陕西举行了婚礼。婚后,夫妻俩感情甚笃,夫唱妇随。1947年冬,戴贤因不愿打内仗,带着三个孩子,一家五口返回古市老家,决定返乡经商。 不料,戴贤将所有的金条到西屏兑换成钞票后,却在回来的途中丢失。回乡后的戴贤又迎来小女儿的出生,一家无房无田无职,只等这些钱经商维持生活,现在全家都陷入窘迫的状态。就在这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到二十三军军长从赣南拍来电报:“委任戴贤为二十三军通讯营长,接电速赴军部报到”戴贤当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于是告别了家人,重新回到部队。谁也不曾料到,这一走,一家子要隔36年才得以团聚。 而在这36年中,张玉瑛一人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既做过又苦又累的敲炭的活,又经受着乡人对她这个有海外关系身份的排挤,几十年来,很多磨难如幽灵如影相随,但无论时局如何,张玉瑛都没有选择与孩子的父亲断绝关系。为了能与家人保持联系,戴贤到了台湾后,就离开了部队,选择从商,再通过各种关系,与家人保持着信件的往来。在隔岸相望的时候,张玉瑛几十年来(除了文革期间断了六七年)从未停止与戴贤写信,她的每一封去信开头都是“齐哥”,落款都是“瑛妹”,三十余年来,两地通信多达一千余件,实为罕见,戴贤一直保存着张玉瑛的每一封来信,1984年首次回乡探亲的时候,将这些信件扫描打印,印成厚厚的三大本交给孩子。 当然,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戴贤后来在台湾成了家,但为了不想对张玉瑛带去打击,一直向她及孩子们隐瞒着,回乡探亲后才将这一情况向两边家人进行了说明,这个晚年还时常捧着世界名著的“百忍世家”的女子心里始终有个结,夫妻俩晚年的时候,为松阳与台湾的亲人恢复联系都做了很多工作,张玉瑛当上了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戴贤作为在台湾的松阳同乡会的两位负责人之一,为无数亲人的相认牵线搭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古市山下阳村一张姓村民要寻找的妹妹居然被他在台湾高层严某家找到,张氏当时在严某家当保姆,并且与严某秘书成了家。 张玉瑛的坎坷半生无疑是那个时代历经的一个缩影,然而在苦难中,她用隐忍和坚强影响着孩子,现在,她的三个已经变成老人的儿子依然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老大已经从教育岗位退休,老二当过油漆工现在沉迷于作画,老三当过建筑工人承包过很多工程,现在喜欢与书法和文字打交道。为了纪念那段时光,张玉瑛的小儿子戴更新花了两年时间写下一本24万字的回忆录《远去的背影》,就是在他的文字里,我才得以认识这个命运跌宕起伏的女子,并对她充满了敬意。 另外一个是与张家墙弄擦肩而过的民国女子叶霞翟。 这只是一个偶然,张玉瑛是张家墙弄的女儿,所以她知道西屏北门叶家与张家墙弄汪家的包办婚姻。出生于西屏北门叶氏家族的女儿叶霞翟从浙江省立处州初级中学师范讲习科毕业后,就在松阳县立成淑女子小学任教,因为母亲是古市人,她早早地被许给古市张家墙弄的大户人家汪连坤为妻。 叶霞翟作为一个接受过新思想教育的奇女子,于1931年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后转浙江省警官学校。关于这场婚姻,只有旧时的古市人有记忆,松阳的县志里只是一笔带过“因不满包办婚姻,只身去杭州”,具体的详情并没有人提及,这一场你情我不愿的婚姻,作为后来成为胡宗南之妻的叶霞翟本人来说更像是一场荒唐的梦。 据说,汪连坤曾多次到杭州找她,均被拒绝接见。再后来,汪连坤娶了第二房太太,生了一个儿子。只可惜,作为地主的后代,他们没有走过那段饥饿的时光。 张玉瑛、叶霞翟,一个是从此处出发,一个是曾经有过姻缘,在她们来去匆匆的身影,为张家墙弄的历史添加了深刻的内容。 作者:黄春爱 来源:松阳新闻网 编辑:叶跃明 吴胜 时间:2018年6月12日
相关新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