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站·浙江在线 浙江网闻联播 《浙江日报》 《丽水日报》 《处州晚报》 ;新闻热线:0578-8061733 8062468 投稿邮箱:zgsynews@163.com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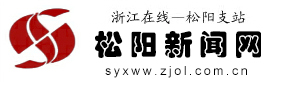 |
|
|
怀念松阳二中 岁月沧桑,我离开母校松阳二中已经六十余年了,但对母校和老师的记忆,却永远是那么清晰、那么美好,想抹也抹不去。 一 1957年下半年,我考入松阳二中。1958年10月遂松合并后,改名为遂昌县第三初级中学。当时学校古木参天、翠竹葱郁,有六个平房教室,面积还不到现在的一半。只有初中六个班,全校师生也只不过三四百人。 校园内有一幢建筑粉墙黛瓦,大门很有特色,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建筑。但大门总是紧闭的,后来才知道,那是正念寺附属建筑——塔院。房子里面有一座亭子一样的六面体单层大石塔,保存着许多和尚的遗骸。后来,学校校舍紧张,师生们破除迷信大胆地拆掉了石塔,处理了石塔内一具一具捆扎好的和尚遗骸,腾出房子作为学校教导处和总务处了。 1958年春,学校开办了春季高中班,有了高中部。1962年下半年,高中停办了。我从初一到高二上了五年学,转学到遂昌一中继续我的学业。 我们真正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时间不多,每个学期都要东奔西跑的,如1957年冬下乡扫除文盲,全班同学被分成几个组,分头到各个村教农民伯伯和大婶们识字。我和十几个同学被分配到赤寿乡半古月村,带队老师是校医周肖轩。当时,我们还是十二三岁的毛头小孩,个子跟讲台桌差不多,却正儿八经地当上了小老师,头尾大概二十来天。 1958年大办钢铁,我们先到那些小山上的乱坟堆里挖坟砖,然后一担一担挑到上方钢铁厂砌高炉炼铁。后来学校又先后组织我们到后周包村和岗下村外的松阴溪溪滩上洗铁砂。之后,大队人马又开赴界首村驻扎,整天在附近山上砍树木烧炭。其实烧炭要有一定的技术,我们这些初中生哪里是烧炭的“料”,只不过糟蹋了一大片树林而已。 除此之外,我们还经常支援各地做水库、夏收夏种及秋收冬种等。我们甚至还挑着行李,步行七八十里路,到南坑源村,帮助当地农民采摘油茶籽,时间个把月。全班同学白天上山采茶籽,晚上全睡在一幢大房子楼上,男女同学各睡一边,中间也没有什么东西遮拦。当时小山村没有电灯,偌大的楼上照明只是在楼梯口点一支小矿烛,光线摇晃昏暗。结果一天夜里闹了个大笑话,一位男同学夜里起来小便,回来后迷迷糊糊的,竟睡到女同学那边去了。摘油茶籽过程中,我们在当地一位老农指点下,认识了不少中草药呢! 那时候,我们是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干的劳动大军。如今回味起来,那年月我们书本上的知识是学得少了点,但对于劳动观念的培养、社会知识的丰富以及劳动技能和体能的锻炼,应该说是大有益处的。 二 当时师生生活相当艰苦,蒸饭用的是一种带小柄的陶罐,后来改用陶钵(土话叫钵头儿),几年后才逐步改用铝制饭盒的。许多农村来的同学,因为家里困难没带多少米,更多带的是番薯或番薯丝,蒸饭时米放得很少,只有多加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吃不饱饭也就不足为怪了。那时候还没有自行车,学生上学来去全靠两条腿。有的同学下雪天没有鞋穿,只好赤着脚来上学。 尽管环境条件如此艰苦,但我们班学习很刻苦,劳动不怕苦、不怕累,同学之间团结友爱,文体活动很不错。在学校举行的班际篮球比赛中,荣获男女冠军。在学校举办的联欢晚会上,曾先后上演过《荷花舞》《筷子舞》以及小戏《三家福》等节目,而且都很受欢迎。 母校每年岁末举行的联欢晚会,更是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晚会的节目都是各个班级自编自演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每次晚会是要举行到元旦凌晨,这时,教导主任郑纵横老师就会宣布:“新年到了!”接着在他的指挥下,全校师生在礼堂里载歌载舞起来,嘴里不停地唱着:“我们是姐妹兄弟,大家团结在一起……”全场一片欢腾。热闹一阵后,学校分给每人一碗又香又甜的红枣粥,至今我都难以忘怀。 初中三年,我们班先后荣获“先进班”“红旗班”和“全面跃进班”等荣誉称号。在一次统考比赛中,因全班总评成绩高,学校特制杜甫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锦旗奖给我们。初中毕业拍集体照时,前面一排同学手上拿的不是锦旗就是镜框,感到特别骄傲和自豪! 那时整个社会物资相当匮乏,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老师们的工资都很低。所以,老师们的生活也一样很艰苦,初二班主任兼几何老师陈如山、图画老师吴定策、刻印蔡琮老师等,因买不起香烟,平时都是抽旱烟筒,衣服穿戴也都很简朴。 记得有几次在老师的带领下,到赤岸畈割稻支援农业,吃饭时间到了,学校工友就会给我们送饭。所谓的“饭”不过是一些受冻过的秋番薯。这种番薯是粮管所按每人的粮食定量搭配的,又细又长,蒸不熟,吃起来“沙沙”作响,有的很苦,咽也咽不下去。老师和学生一样吃,师生间同甘共苦、同舟共济。 三 老师们的每一份关爱和谆谆教导没有因岁月流逝而消失,我永远牢记在心中。 数学老师康来宁,宁波人,矮个子,宽额角,头发较稀疏,但总梳得很整齐。上课时,说一口宁波腔很浓的普通话,思考问题爱看天花板,但他的和善却是出了名的。记得一个初冬的凌晨,我早早地上学,到学校校门仍然是紧闭的。那时还没有门卫,我又敲又叫,把睡在离校门不远的康老师给吵醒了,他身上只穿着单衣和短裤,手提一盏煤油灯,颤颤栗栗地来给我开门,嘴里嘟哝着:“你这么早到学校来做什么哟?”看着康老师受冻的样子,我心里真不好受,忙说:“康老师,真对不起!”康老师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 语文老师郑朝鸿,淳安人,中等略高,脸庞消瘦。眼窝微凹、高鼻子、尖下巴,留西洋发,给人一种很精干的感觉。1957年他一毕业就分配到二中,成为我们的班主任。他和我们的感情很深,尽管那时我们顽皮,但他总是那么慈祥和蔼,很少对我们发脾气。学校新造校舍,发动师生自力更生到赤寿砖瓦窑挑砖头。学生最多挑八块十块的,而郑老师一挑就是二三十块,我们佩服至极。 体育老师杨汉遗,诸暨人,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颧骨较突,背稍有点驼,但说起话来铿锵有力,从不拖泥带水。他为人耿直,性格开朗,平时和学生亲密无间,但上起体育课来却一丝不苟、严厉有加,我们都不敢在他的面前调皮捣蛋。记得有一段时间,他带我们到樟溪钟家村(福村)帮助农民搞秋收。每当我们拔完一丘田的马料豆时,杨老师总是在田中央手舞足蹈,嘴里不停地唱着:“胜利了,胜利了,笑哈哈!胜利了,胜利了,笑哈哈!”同学们都被他那滑稽的动作和高兴的样子逗得哈哈大笑。刹那间我们的疲劳和辛苦就全都消失了。 初三班主任、地理老师叶昌梓,望松乡人,大个子胖乎乎。两颗门牙微微外露,冬季头戴一顶褪了色的蓝色工人帽,身穿一件旧棉袄,罩一件同样褪了色的蓝中山装,使人感到分外的朴实本分。他的地理课上得很生动,同学们都很喜欢听。上劳动课时,他总是用美好的前景来鼓舞我们的士气,逗得大家心里痒痒的,似乎美好生活马上就要实现似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兴奋,干起活来特有劲。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感谢母校松阳二中,也感谢辛勤教诲我的老师!松阳二中,一个永远值得我怀念的地方! 作者:杨致良 来源:松阳新闻网 编辑:肖土根 孙志华 吴胜 时间:2025年4月17日
相关新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