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站·浙江在线 浙江网闻联播 《浙江日报》 《丽水日报》 《处州晚报》 ;新闻热线:0578-8061733 8062468 投稿邮箱:zgsynews@163.com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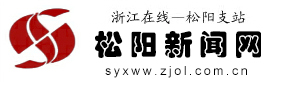 |
|
|
古市手工业合作化的故事 一 1962年,我初中毕业后,因为父亲在台湾,不得不辍学在家。我们家无田无地,面临如何生存的问题。古人道:“学问是济世之本,技艺乃谋生之道”。前者对我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缥缈幻想,后者才是我切合实际的选择。 有一天,我碰到同班同学叶庆同。他告诉我已经到古市建筑社做泥工学徒,师傅叫徐坤忠。受他的启发,我产生了去做手艺的念头,后来打听到建筑社的廖聪友师傅要收一名学徒的消息,我便壮着胆子到廖师傅家毛遂自荐。当时廖师傅是古市建筑社的主任,有一手出众的木工手艺,为人正派,处事大方,很受同行尊重。头一次见面,他开门见山地问了我家及个人情况后,感到很满意,当即决定收我为徒,让我第二天就到古市小学工地上班。 当时我是廖师傅以个人名义收的学徒,还不是古市建筑社的职工。我心里当然很想当学徒时就成为古市建筑社的正式职工,但嘴上不敢说出来,好在师傅也是这么想的。当时集体企业招工,虽然没有现在这样要经过县人事劳动部门下达招工指标,并进行严格考试和审核批准的繁琐程序,但也要当地政府同意后才能成为正式职工。我的招工报告上去后,镇里迟迟没有批复。镇领导都认为我的社会关系复杂,主要是指我父亲在台湾,不适合在集体单位工作。这件事拖久了,我的心情忐忑不安,不知怎么办才好。 师傅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认为我做事勤快,而且脑子比较灵活,和工友们相处得也很好,舍不得我走。于是有一天,师傅跑到镇里发火,撂了一句狠话:“做手艺又不是当官,招一个‘斧头坯’有这么难吗?我不管你们批不批,这个人反正我要定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廖聪友当时还是古市手工业系统十三个单位的党总支书记,他说话是有一定分量的。如果我当时跟一位普通木工师傅,肯定得走人了。幸好我运气不错,廖师傅的那句狠话起了作用,最后镇领导勉强同意了。就这样我成为古市建筑社一名正式职工,等于是有单位的人了。 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当然是倍加珍惜,从此工作更加努力。我为了多学手艺,尽快掌握技术,不懂的地方就问,然后自己反复推敲琢磨,在实干中积累经验。经过三年的学徒生涯,在师傅的精心指导和个人的勤奋努力下,我终于成长为合格的木工师傅。 师傅对我有恩,与我情同父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师傅的恩情,特别感谢他在我处于困境时给予我的信任和帮助。学徒出师后,仍与师傅保持密切关系,后来我干脆租住在十三弯墙弄内,与师傅一家成了隔壁邻居。平时吃饭时,我喜欢端着饭碗往师傅家跑,为的是听师傅和来他家的很多同行和朋友们聊天,增长见识。不久后我就独立担任了建筑工地的木工组负责人。之后,我又自学了细木工技术,成为“大木”“小木”兼具的熟练木工,在行业中逐渐积累起了名气。 师傅手艺好,为人随和,处事精明干练,在古市手工业系统威望很高,深得同行们的尊重和信任。大家乐于与他相处,他家几乎每天都是高朋满座,非常热闹。这种场合我参加多了,不仅认识了古市的很多手艺人,而且慢慢知晓了古市一些手工业单位的情况。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古市镇虽然是个小地方,但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各行各业一个也不少,而且它们个个都有渊源。 二 松阳手工业有悠久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手工业涉及的各行各业都是以个体分散经营的方式生存的,在没有重工业的旧时代,手工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地方经济有相当大的贡献。据统计,松阳手工业的产值占到全县工业总产值的九成,足见其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但是手工业者的分散经营以及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手工业经济像小农经济一样没有多少前途。1953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手工业社会主义合作化改造。松阳县成立了手工业联社,古市镇成立了铁业社,17个古市打铁师傅全部进入古市铁业社。铁业社就设在三角坛,负责人姓徐,不久就去世了。后由林周根继任,并增加了锅炉小组,铸造铁锅和主要生产犁头等农具。随后,古市镇缝纫社也在太保庙对面的五间店面开张营业,此处原是刘家祠堂。缝纫社的负责人是郑方进,他性格温和,为人通达。谁都知道,缝纫社大多数是妇女,争吵之事时有发生,多亏郑方进从中调和及时化解矛盾,大家得以团结共事。 1954年,县里成立了手工业劳动者协会,西屏镇、古市镇、靖居区设立了手工业劳动者协会分会。接着,政府又成立了手工业联社。在此形势下,古市手工业各行各业闻风而动,在1955年前后,相继成立了建筑社、篾业社、造纸社、木器社、豆腐社、理发社等合作社。能够称为社的,一般来说人数都在二三十人以上。人数少的行业,就成立手工业合作小组,比如当时古市就成立了钟表组、刻章组、金银店组、白铁五金组、印染组、砖瓦组、弹棉组和棕板组。这些合作社和合作小组,几乎涉及古市手工业的各行各业,至此,古市手工业进入了合作化时期。 古市手工业各单位接受行政和业务的双重领导,行政上归属古市镇政府领导,业务上接受县手工业联社管理。1958年6月,县手工业联社撤销,所属企业归县工业局管理。1982年,县里设第二轻工业局负责全县手工业的管理。县里成立手工业联社后,为了加强重点区域的管理,在古市设立了手工业办事处。首任办事处主任是义乌人楼章立,此后继任者有尹关元、王一清等人。他们都是不摆架子的人,比较讲究工作方法,经常到各社负责人家里走访,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都是在走访中商量解决的。各位主任走访最多的就是我师傅廖聪友家,因为我师傅是古市当时最大的手工业合作社建筑社负责人,手下社员光木工和泥瓦工就有三十余名,加上他管理能力强,建筑社以义务工形式,在横街闹市区盖起了200多平方米的社场。该社场在街道改造时拆除,后又在筏铺盖起了2000多平方米的新厂房,锯板、油漆、金工等车间一应俱全,业务红火,成绩斐然。 三 手工业合作化初期,由于社员成分复杂、经历不同,对管理工作是很大的考验。换句话说,各合作社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关键在于负责人是否能干。所谓能干,首先技术上要胜人一筹,让大家服气;其次处事要公道,能以德服人。我师傅廖聪友就具备以上素质,所以建筑社发展得红红火火。当然古市的其他合作社也有能人。比如篾业社的丁少清就很能干,见多识广,能说会道,特别擅长做思想鼓动工作。在他领导下,篾业社二十多位社员各施所长,生产了大量农业生产需要的谷簟、建筑工地的脚手架篾垫,以及老百姓居家生活需要的竹器产品。在满足市场需要的同时,也为合作社增加了集体收益,篾业社得以从原先的大井头小社场搬迁到筏铺的新厂房。再如造纸社的负责人王香元也很不错,他是一位话不多但能一锤定音的主,手下职工大多是青田人,大家团结齐心,事业慢慢做大。造纸社从下街水碓边,搬迁到筏铺新厂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稳步提高。 几个合作社负责人各具特色。木器社的第一任主任叶荣光,大家都叫他“拼命三郎”。他做圆木出身,一身好手艺,手脚特别麻利,一天的生产量,普通师傅要两天才能完成。可惜叶荣光的性格太直,听说是顶撞领导的原因,被下放到农村去了。他离开后,木器社先后有戴岩松、周贤森、周贤明、金龙等人继任。社场先是在后街罗家宅旁边,1972年毁于一场大火,一直没有能力恢复。几年后,经镇政府协调审批,在筏铺新建了厂房,木器社改名钢木家具厂,后因经营不善,负债累累,1993年宣告破产。 豆腐社负责人是宋长清,他虽患有足疾,但做豆腐技术一流,他与我师傅关系不错,常到十三弯师傅家坐。豆腐社的社场在大井头上首,做豆腐要到程家埠头挑松阴溪里的水,当年松阴溪的水清澈见底,很适合做豆腐,豆腐社生意一直不错。 理发社在水弄头老桥边上,是古市最热闹的地方,社员大多是青田人。理发社的负责人占岳松,个子矮矮的,是一位忠厚之人,和我做过邻居。因为理发社身处闹市,消息传递快,这里相当于古市的“新闻发布中心”。理发社店内的土风扇令人印象深刻。那年头没有电风扇,盛夏季节,店里的纳凉就靠用纸板做成的土风扇了。理发时,一人负责理发,另一人不停抽拉绳子让纸板左右送风,享受“高级”服务的顾客,闭眼靠在椅子上,舒服得跟“皇上”一样。 我记得修钟表和刻章、做雨伞的人组成一个小组,店址在下桥头饮食店对面,负责人是徐荣华。他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写得一手好字,兼做对联生意,在古市手工业圈子里算是一位“文化人”。修钟表的生意有一段时间很好,但随着手机普及,戴手表的人越来越少,修表生意一落千丈。 五金小组由打金银和敲白铁、修锁等行业人员组成,负责人是温怀达。他精明能干,在古市也算是一位老江湖。后来,这个合作小组并入钢木家具厂了,最后接受了破产的命运。温怀达从此就歇业了,好在他家子承父业,在观门口开了一间打金店,生意兴隆。 砖瓦小组的瓦窑在木圩头,主要生产小青瓦,小组负责人是李金元,樟溪人,身材不高,却力大无比,是做瓦的一把好手。他的搭档叫李光贵,也是樟溪乡人,两人合作,一度生意红火。但随着造房子普遍用钢筋水泥后,小青瓦用得很少了,这个行当也就基本消亡了。 时代变迁,往事如烟。现在回过头看,仅仅一个多甲子的时光,一度兴旺发达的古市手工业在合作化改造中得到新生,在企业改制中消失。作为这场变迁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我的内心时常涌起许多感慨,对当今社会快速发展和进步充满了喜悦。 作者:戴更新 来源:松阳新闻网 编辑:肖土根 孙志华 吴胜 时间:2025年5月8日
相关新闻 |


